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No. 2009-03
转自:中国工人研究
路爱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中国改革已经持续了30年,学术界出现了很多对改革的理论总结和反思。本文提供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作者纵向对比了改革前后的各类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横向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对改革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应该以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对未来改革走向的判断也应该以此为依据。
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一场大革命的后果,用翻天覆地形容殊不为过。国内外的各种评价潮涌而来。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成功地把计划体制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个步骤渐进而后果激进的转型过程不但没导致经济下降,反而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的改革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奇迹。但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文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滞后,由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尤其近年来,质疑之声由小变大,由弱渐强。有些人认为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无损于改革的巨大成功,需要而且能够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表明中国增长模式难以持续。[1]
中国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的理解自然不完全一致,但如下说法有可能得到了广泛认可:1978年正式开始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到今天,这个过程可以说基本完成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就实现这个目标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不过,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今天中国确实出现了两极分化,也确实产生了“民营企业家阶层”即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改革进行反思呢?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一个不常用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改革,分析和回答改革后的中国“是怎样”的问题。这个视角就是: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3]本文将论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今天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上,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一般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同,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与这类国家相似。正因为如此,采用“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标准,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更合理地解释改革过程和目前状况,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实际的估计。
一、制度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过不到30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到改革前夕,按人均GDP衡量,中国无疑属于低收入国家,但它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发展中国家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体制、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上,都更接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实行经济计划而不依赖市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制度特色。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是既不与西方也不与苏联阵营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发展中国家。就此而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说,是“非正常的”。
不但中国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它们根据中国的这些特征评判和预测中国的行为,确定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例如,美国政府把中国叫做“红色中国”、“毛的中国”或者“共产主义中国”,长期以来拒绝给以外交承认,坚持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敌对行为,显然并非由于中国的经济不发达,而是由于它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异类,当作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总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特色,无论中国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把中国当作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1978年开始的改革把中国带入又一次历史性转折之中。改革开放30年后,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表明了怎样的历史走向,迄今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发展经济”的目标很明确,其它一切则似乎仍处于“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宣布改革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其特征或质的规定性,似乎完全由中国本身的现有状况决定,即改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什么样子。
(一)经济体制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年到2005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万家减少到12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4]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8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2005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65%;2005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计算,2004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2007年3月16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
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中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相应扩大市场力量,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
如果说,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那么,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可谓应有尽有。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2008年2月末,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77个国家的承认。[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因此,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
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
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二)政治体制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为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9]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三)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后来被不无贬义地叫做“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1951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这一点,也为中国转上市场经济之后自身的实践所证明。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
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
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到2006年,全国还只有25%的劳动力享有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劳动力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更低。[10]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当个人财力不再能解决生老病死、上学升学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好求助于所谓“好心人”,寄希望于他人怜悯出手相助,这就产生了重建所谓慈善事业的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后,经常性的社会募捐不但用来应对突发灾难,而且成为解决常规发展问题筹集资金的手段,例如用来资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并成为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后的“新生事物”,在“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尚且能够提供社会保障,而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今天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社会特征
由于改革前的中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成就明显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个时期,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进入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一举逆转了中国百年来的经济颓势。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1.4%,大大高于同期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快速赶超势头。邓小平在1979年对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11]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是实事求是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惠及全国人口,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到计划经济后期,中国的一系列人文发展指标明显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1980年在对中国的经济考察报道中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在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比其他穷国同类人好得多。”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的第十版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12]
改革后,中国以渐进方式对原有体制进行了根本改造。在没有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来,GDP保持着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大致在10%,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成为改革以来最大的亮点,也是改革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对改革不满甚至抵制情绪始终挥之不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们一方面认可经济增长改善了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不满随之出现的某些社会现实例如两极分化。进入21世纪后,这种不满似乎转化为更加强烈的质疑,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委婉承认“不科学发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表示了加以矫正的意愿。
但是,公众甚至政府不满的问题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一些人之所以难以接受,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沿用社会主义标准判断中国改革后的发展,认为这类问题不应该出现而出现了。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其参照对象只能是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综观世界,在任何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所有这些社会现象不但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经地义、必然存在的。否则,它就算不上是一个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只要看看与中国同属低中等收入一类的国家就很清楚了,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印尼、伊朗、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13]所有这些国家无不存在着类似中国的社会现实,包括下面将要分析一些经济社会特征。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常规。因为建立了市场体制的中国只不过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不具备这类经济社会特征反倒不合常理。
(一)经济边缘化
GDP的高速增长被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据。然而,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14]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许需要首先简述如下常识,即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劳动分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夺停止之后,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有效地维护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分工。长期发挥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分工劣势之中,没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链条上。几百年来的经济史表明,无论如何起劲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鲜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它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动摇自己的优势地位。[15]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意义在跨越常规,为尽快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当高的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到改革前夕,中国已经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边缘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超常规”发展战略使中国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就拥有了核武器,成为多年来世界核大国中唯一的低收入国家,在科研领域也推出了世界级成果。因此,尽管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于其他边缘国家,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却类似半边缘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例。与同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超出印度,不但人均收入超过印度,工业化程度更是远远高于印度。
改革后,中国开始把追求GDP增长放在首位。为此,中国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大量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1980-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5.6%,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结果,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大约7%,
在全球排名从第22位上升到第3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到2005年,外资在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税收总额、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支撑着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16]按照外贸占GDP的比重衡量,目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明显外贸导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认为严重到患上了“外资依赖症”的地步。[17]
经济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并不难,因为强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本国经济开放度,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则通常难以抵御内外压力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打开国门。但是,对外开放程度并不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它们目前的开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很大差别,甚至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反倒是高度开放的。需要分析的是,外向型增长模式是否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是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还是越来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
判断一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有一个简单标准可做参考,那就是该国基本出口产品的结构或类别。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构成衡量国家的生产力,发现它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富国的出口产品往往类似其他富国的出口产品,即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产品的结构高于人均收入通常预示的水平,说明该国生产力超过人均收入水平通常达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1992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类似于人均GDP比中国高6倍多的国家,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能力,生产力表现出半边缘国家的特征。然而,这个优势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扩大,而是逐步缩小了,尽管与类似人均GDP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仍然要好一些。[18]
中国产业优势逐渐下降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强调运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以便充当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中国竭力维持低工资。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国内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世界市场则难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进行恶性竞争的陷阱。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所谓“竞底”或“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国比的不是谁生产力更高,产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资本更雄厚,而是比谁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国劳动力,更能容忍对本国资源环境的破坏。事实证明,这种朝向工业文明底线的竞争不但不能提升一国的地位,不能使之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使之陷入不发达陷阱难以自拔。如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内市场同样充斥着外国品牌的各种产品和消费品,许多原先著名的国产品牌大多已销声匿迹。中国可以大量出口,本土产业却不能制造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产品,“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GDP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增加,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一直到1820年,即西方工业化开始后二十多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50%以上,是整个欧洲的1.22倍,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洲,出口制造品世界第一,当时的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制造”。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弱国,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击。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但经济结构恶化,对外依附性增加,国内消费规模得不到相应扩大甚至相对萎缩。在某些方面,其日趋边缘化的增长模式与成功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日本。[19]经济结构趋向边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是拉近了与“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的距离。
(二)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
改革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国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没有发生革命、没有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面貌在不到20年时间发生如此巨大改变,的确不同寻常。很多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有关改革的正义性问题不时被提了出来。
放眼世界,人们很容易发现,如果说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异乎寻常,那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高度不平等状况则完全不是特例。无论经济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平等。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南非。发达国家中,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国,但也有更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欧和欧洲实行福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样说来,没有如此明显的收入差距,中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来源提供的具体数字不太一样,但有几点不存在很大争议: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属于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第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惊人;第三,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世界组织以及各种研究都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有研究表明,自1992年以来,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等于或者大于0.4,2004年达到0.4418。[20]亚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位居亚洲第二,超过了除尼泊尔之外所有亚洲国家。[2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显示,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2-0.3,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类似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那时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差别,根源主要是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改革后,无论城乡还是城乡内部的收入差别都显著扩大,推动整个国家贫富分化加剧。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例为1比2.57,到2004年已经扩大到1比3.21。在城镇人口中,1997年最低与最高收入差距是4.22倍,到2004年,两者的差距拉大到8.87倍,7年扩大了1倍多。[22]据称,鉴于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当一部分属于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可能比显示出来的更大,城镇人口高低收入估计可能高达12倍以上。
在世界银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国家排位中,2005年中国在120个国家中排第85位,在中国后面只有35个国家,其中32个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大于所有已经转上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休克转型中以造就金融寡头著称的俄罗斯,也大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问题不是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是在贫富差距上赶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极端的国家。
收入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分化不亚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富豪阶层,从各级政府干部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大小企业管理者到工程技术权威,从各类专家学者到著名文艺体育界人士,这些传统上被视为社会精英的阶层,当时却并不拥有传统上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财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无财富。社会“精英”的这种状态堪称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特色,在任何“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后,一个新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重新崛起,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与世界上流社会的接轨。这个新富阶层在财富水平、消费模式、生活方式、趣味爱好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世界各国的上层越来越接近,而与本国的工农劳动阶层越来越疏离,虽同为国人却实际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007年,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这个所谓“中国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23]在中国13亿人口中不足0.4%。尽管如此,就绝对数量来说,中国的新富阶层人数已然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中等大国。这个比例极小而绝对数庞大的新富阶层拥有巨大消费能力,成为国际奢侈品销售商的新宠。改革近30年来,中国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过是美国人均财富的2%,但中国近年来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
中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1,759元(大约相当1500美元),同期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更是只有3,587元(不到500美元)。就在这样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却造就了世界级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年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全球946名富豪榜上,中国大陆与巴西和西班牙一样,各拥有20人,超过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等国家。[24]另据统计,2007年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25]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有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市场经济中,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弱国穷国照样能够出产超级富豪,少数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逊色,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无疑,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接轨。
富人阶层的另一端是贫困阶层或所谓“弱势群体”。他们中除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边缘人群例如乞讨、流浪者之外,主要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广大劳动者。也可以说,除了比例极小(尽管绝对数量可观)的暴富阶层以及大约15-20%的所谓中产阶级之外,其余人口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态虽然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弱势,那就是,相对于有产者特别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绝对劣势,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缺乏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等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
与富翁群体一样,弱势群体也是改革后出现的“新兴”阶层,是社会分化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新兴”群体的出现在农村与解散集体经济、重返个体生产有关,而在城镇,则是企业改制或私有化的直接后果。企业改制导致国企纷纷败北,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或者关闭或者转为私人所有,导致职工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流向了社会底层,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弱势群体。他们丧失了原有就业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越来越向原来就缺乏这些保障的农村进城劳动力靠拢。这个群体距离赤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改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较平等,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到20世纪末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政府目标宣告破产。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2006/07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4800万,其中农村2600万,城镇22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7%。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很低,远远达不到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费1美元的水平,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如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约为1.35亿,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26]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专家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在2001-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还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再次表明,贫困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水涨船高。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据说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这也许算的上中国改革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经济增长与贫困共存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顽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过中国的拉美地区,早就存在这种所谓“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困现象恶化。看来,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是否增长,都必须接受社会两极分化这个后果。
(三)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
与发达国家的无产者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高比例的半无产者。可以说,如果无产阶级化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变化的主要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改革期间,在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的“工业化”浪潮中,中国的劳动力具有这一特征。
一般认为,工业化伴随着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即小生产者被剥夺,使之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或者通常所说的工资,必须足以维持劳动力基本生存和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综观全球,基本实现了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能够完全依靠工资所得和基本福利来供养家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劳动群体却生活在半无产者家庭中。他们除工资之外,还需要而且必须从各种兼职中获得收入,包括小农生产,因为他们的工资通常低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的水平。这种状况是世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不在于把劳动力变成无产阶级,而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半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维持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27]
与无产阶级化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劳动条件更恶劣,更缺乏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在低于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水平上之所以还能生存,完全是由于他们和/或家庭在这份工作之外,还通过其他劳作获得收入,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就业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养本来应该计入劳动力成本,但他们得到的低工资不足以支付这一部分费用,因此,半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参加劳动,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发展中国家以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为特色,这些劳动力大量表现为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人、兼职工人等。
1949年之后,中国迅速消灭了血汗工厂,加速进行的工业化把大量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很快覆盖了各类企业的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条件显著改善。保障就业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铁饭碗”,劳动者没有失业之忧,享有与就业相联系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下,工人获得了与西方现代工厂不相上下的劳保条件,在有些方面,例如工人的劳保医疗,甚至比有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当年的一些工厂更优越。产业工人能够完全依靠本职工作所得,保证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说,在获得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和其他报酬这一点上,当年中国工人阶级更接近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状况,劳动力朝无产阶级化的方向演进。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完全农民身份的劳动力。
改革中断了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过程,使之转上了半无产阶级化的轨道。改革以来,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劳动者身份地位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职工的“铁饭碗”被砸碎了,劳动力的就业取决于资本需求,工资随行就市。中国不但产生了固定的失业大军,而且,随着劳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当多就业人员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口。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兼职工等越来越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劳动力进入半无产阶级化过程。[28]
中国半无产阶级大军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典型的半无产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家里有地,本人在城镇和/或工矿务工,部分家庭成员还留在农村务农,他们的流动性强,工作和生活极不稳定。中国的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后劳动力变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
首先,农民工在数量上举足轻重,目前规模估计为1.3亿左右。按2005年中国2.7亿城镇就业人口计算,几乎占了半壁江山,[29]他们大约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8%,加工制造业的68%,在服务行业也超过一半。
其次,他们的工资水平低,处于非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底层。有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年薪大约是国有企业职工的53-55%,而在传统服务业中工作的大多农村妇女的年收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还低很多。这种工资水平实际上低于劳动力成本,远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工的报酬水平大大低于劳动力价格,使他们难以在就业的城镇地区养育家庭。因此,长期的城乡分居就成了农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农村收入的补贴,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据统计,目前农民纯收入中40%来自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获得的工资。
第三,他们是改革后大量涌现、遍及全国的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主力军,是城镇建筑业以及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通常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障,不享有任何医疗、教育等福利,也没有工伤、养老保障。他们在缺乏基本生产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工作环境最恶劣,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是工伤、职业病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最强,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区、行业、城乡之间流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带有季节性特征,因为他们需要兼顾留在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
第四,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稳定、工作技术含量低等原因,他们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几乎完全不具有与雇主/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遭受资本无情驱使和最大限度压榨的劳动力群体。对很多人来说,能够按时拿到微薄的报酬已属幸运,因为工钱被克扣的现象长期、大面积发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讨工钱,甚至反遭迫害。
第五,他们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难和压力。家庭成员长期离分给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伤害。被迫留在农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着残缺家庭、留守状态带来的额外生活压力和痛苦。有资料显示,2006年在外出务工的1.3亿人中,已婚者有1.06亿人。除去举家迁移的大约3900万人,只有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00万人,以70%男性计算,农村仅“留守妇女”就有4700万人左右。[30]有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留守儿童”大约为5800万,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他们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码条件。[31]
正如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也成为了一种统计常态。西方一些组织以及政府热衷于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批评中国劳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产物。不过,血汗工厂在中国重新出现并迅速扩散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虽然在1995年颁布实施了《劳动法》,但《劳动法》迄今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大量劳动力的工资所得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政府执法不力外,一个深层原因是,没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今天的中国并不例外。
(四)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和赞扬。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人文指标的进步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寿命、普及教育、减少文盲、婴幼儿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国家。
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2]此外,1960-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33]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改革30年,中国的GDP高速增长,2004年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10倍多。中国无疑比过去更富有了,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了,按常理推测,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将在原有基础上出现更大跨越。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超前性越来越小,即越来越接近其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在某些人文发展指标上,例如在人均寿命增长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进步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领先者落到了后进行列。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中国的表现不但与GDP快速增长不相称,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34]
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增加了33岁,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2.9岁,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4.0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5.4岁、南亚的8.9岁、中东和北非的9.1岁,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9岁。比中国表现更糟的只有两个地区,即欧洲和中亚(增长0.3岁),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减少2.5岁)。这两个地区不但没有能与中国一比高下的GDP增长,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欧洲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转型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导致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35]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3年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千分之3(从8下降到5,为2002年数字),中等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2(从42下降到30),低收入国家为千分之15(从95下降到80),而中国仅为千分之9(从39下降到30)。从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1990年好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2003年则与之拉平,进步速度明显放缓,进步速度更是远远落在低收入国家后面。中国的表现似乎只好于高收入国家,但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继续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并不具有可比性。同一个来源数据还表明,在这一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36]
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高自杀率等等。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个国家中的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而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一直接近60%。[37]
改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进步同样不符合预期。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80%。经过不到30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农村下降到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34.9%和67.3%,埃及分别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16.8%和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
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30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年,根据当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6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10%。[38]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15.0%的印度。[39]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1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国越来越回归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衡的状况。也正如在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40]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2015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
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诚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总体水平尚不处于明显劣势,但与GDP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相比明显滞后。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但难以建立“支持导向”的人文社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五)政府能力弱化
新中国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在历经百年积贫积弱之后,中国拥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如此有效的领导作用,以至无论人们对这个阶段的评价如何,几乎都有理由把各个领域的成就或失败与政府直接联系起来。相应地,政府似乎理所当然地承受一切,因为除政府以外,似乎没有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可供推委责任。
历史表明,当年中国政府既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案有效地解决面临的近期问题,也有能力制订和实施长远发展规划,并坚持不懈地进行长期努力来实现既定目标。也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创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经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由于某些政策不当,政府独揽一切也造成了一些立竿见影的不良后果。但是,作为一个强政府,中国政府的能力还表现为能够迅速纠正不当政策,在短时间内扭转局面。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不具备这种能力,还有不少政权甚至长期不稳定,难以行使正常的政府职能,因而被称为“失败国家”。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则普遍拥有较强的政府,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政府一般具有较强的市场操控能力和多样化的社会控制手段。政府的强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区别强国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改革在政府一手主持下展开。能让中国这条大船平稳掉头,改变航向,直到2008年没发生社会断裂或经济大衰退,反而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表明中国政府的能力相当强大而有效,尤其是在改革前期。但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政府能力就是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一个强政府意味着,它能够确定基本经济政治目标以及战略战术,能够实施相应的决策,并能够动员各种资源完成这个任务,得到希望看到的结果。拿这个标准衡量,改革后中国政府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每况愈下。
转上市场经济轨道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政府似乎接受了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开始把自己定位于市场的经济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撤消经济计划,实行政企分开,逐步从经济生产领域退出,把配置资源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行分权化,扩大地方政府权力,减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等等。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导致两个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突出后果。一是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膨胀。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员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时,行政经费出现惊人增长,1978年到2003年,中国GDP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1.2倍,而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在一份包括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23国统计中,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超过中国的只有一个国家,而政府雇员报酬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中国的也只有4个国家。[41]另有资料显示,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6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长23倍。[42]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变成了一个成本昂贵、资源耗费越来越多的政府。
转换政府职能的第二个结果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明显削弱,地方利益坐大,以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倾向于摆脱中央约束,各自为政。这不但使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措施难以贯彻实行,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不能有效地甚至完成份内的职责。2007年上半年,中国媒体披露山西存在奴役劳工的黑砖窑,人们震惊于现代奴隶的非人遭遇,更愤怒于地方政府长期不作为,致使如此赤裸裸的人身压迫持续多年。但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黑砖窑映射的与其说是基层政治的腐败,不如说是基层政权的溃败,也就是“政府公共职责的全面丧失,基层社会生活秩序的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的根本性缺失。”[43]
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是全方位的,表现为政府不管的事情大大增加,政府想管而管不了的事情也大大增加,而政府实现预定目标的记录越来越差。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尽管仍然有能力提出目标,实现目标的能力却每况愈下,使越来越多的目标、政策和措施停留在口头上和书面上。例如:改革之初,政府正式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将近30年过去了,却只见有先富,不见共同富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国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政府在1994年郑重提出,要在20世纪末基本消灭贫困。[44]1997年共产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这个目标,庄严宣告:“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些宣示,被普遍理解为中国“要让贫困连同二十世纪一起成为历史”,或“决不把贫困人口带入21世纪”。但随后的发展表明,贫困并没有被消灭在20世纪。直到今天,不但农村存在贫困人口,而且城市也出现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绝对贫困人口。[45]贫困问题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痼疾,政府也不再提彻底消除贫困这个目标了。
在教育方面,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在20世纪末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就是著名的“两基”规划。但直到今天,中国仍然不能保证全部适龄少年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2007年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为84.14%,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欠债高达500多亿元。[46]目前,中国6岁以上人口中每12个人就有一个文盲。政府提出把文盲消除在20世纪的目标也以失败告终。
政府曾强调在发展中搞好生态环境治理,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老路,先后制订了一系列河流、湖泊的具体治理计划,投入很大财力。但实际上,被要求限期整改的项目往往只见投资不见治理效果,期限过后污染依旧,甚至更为严重。例如,限期治理淮河、太湖都已失败告终,饮水、空气、土地等污染严重,环境安全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不断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政府曾许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这个目标,把它说成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7]1982年共产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人们才越来越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日益沉重,以至形成了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距离小康社会仍然遥远。2007年,共产党十七大提出要建设“五有”社会,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很清楚,一个不能保证国民“五有”的社会很难算得上小康社会。
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上曾得到国内外不少赞扬,但这种能力也在明显下降。例如,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控制在8%左右,避免所谓经济过热,结果当年GDP增长超过11%。2007年这种局面重复出现。面对与所定目标脱节的结果,政府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当作了自己的工作成绩。对待近年来急剧上升的房地产价格,政府同样表现了类似的行为方式,三年调控无功而返,“调控”被民间讥为“空调”。政府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不但缺乏所谓“核心技术”,而且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没有产生任何世界级科技发明。而计划经济时期反而有这样的成果,例如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激光照排等。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改革后立法突飞猛进。法律虽然多了,法律法规得不到切实执行却越来越变成寻常之事。例如,199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被认为标志着“中国劳动法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劳动力地位的提高却没有随之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相反,建国以来,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还从来没有像改革期间那样遭到如此程度的损害,否则,也就不会有大量血汗工厂的建立和长期存在。在大量法规条文出台的同时,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甚至假文凭、假学历、假证件、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成果、假广告等等,各级政府屡屡打击却是屡禁不止。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有些地方公开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却长期不予或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包括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兴建超豪华办公大楼,不惜大量举债,但这种明显的越轨行为长期得不到制止。
政府能力下降在生产安全上表现尤为经常和突出。改革后,中国煤矿矿难不断,每年死伤人数高达30万,为世界之最。到2007年,经过下大力气整治之后,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仍然为发达国家50倍,甚至为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南非的4倍。另外,有些行业的事故还在上升,比如2006年危险化学品事故上升了16%,烟花爆竹事故上升了24%,另外有一次死亡3个人到9个人的煤矿重大事故,也上升了22%。每次发生重大矿难,政府都会“采取果断措施”,“积极组织抢救”,同时追查责任,表明彻底整顿的决心,但矿难在政府官员的怒斥声中照样发生,政府的承诺越来越像一张空头支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曾迅速消除了被认为根本无法消除的社会现象,例如娼妓业、赌博、吸毒、性病等。改革后“黄赌毒”卷土重来。到今天,其他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所有罪恶行当和“职业”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这些“新”行当有贩卖人口、黑社会、吸毒贩毒、赌场、夜总会、卖淫嫖娼等,“新职业”则有职业乞丐、流浪儿、童工、奴隶工、包工头、保安、三陪女、舞女、二奶、垃圾王等等。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导致社会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镇的防盗门窗成为大众自我防护的无奈选择,也显示了公众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总之,从庄严承诺的大政方针例如不搞两极分化,到政府限期目标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治理污染等,甚至小到市场监管例如食品安全、包装和建筑材料标准等,政府越来越说得到却做不到。政府甚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员。改革以来,官场和官员腐败不断升温,以致中国由一个清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早在1995年已经成了极端腐败的国家之一,到2006年,仍然被认为是特大腐败国家。大面积、难以遏止的腐败表明政府治理不力,反过来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削弱政府动员群众的道德力量,导致政府权威进一步下降。腐败过程中官商结成的利益链条渗透到各个领域,建立各种利益联盟,盘根错节的裙带/权贵资本主义令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难以奏效,以至人们感叹“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脑袋指挥不了四肢。
在国际舞台上,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开始接受西方援助,1995年甚至成为世界最大的受援国。援助方对中国的发展自然有它们的目的和愿望。一项研究表明,正像援助方所希望的那样,在华外援项目不仅成功地引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还引入了政策改革。“外援在中国的活动和外援的方式为中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方法,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8]接受西方援助,听从西方建议,也许不一定必然削弱政府能力。但事实是,尽管不断声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却不仅没有能力实现对国内人民的许多基本承诺,而且越来越没有能力实现在国际上的许多重大承诺,例如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新千年目标、保护知识产权等等。在开放政策指引下,改革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事事处处强调“与世界接轨”,主动接受西方援助等。这种模式的中外互动增加了外部力量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对政府决策和行动能力形成一定制约。
当然,目前的中国政府还远不是一个典型的弱政府,中国更称不上是“失败国家”。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的国家动员能力仍然比较强大,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对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上,例如在抗击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中,政府都发挥了相对有效的组织领导作用。但是,政府能力下降的趋势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有能力组织力量抗击非典,却不能有效控制某些重新抬头的传染性和地方性疾病,不能保障人人病有所医;它能够抢险救灾,却不能有效维护例如煤矿的生产安全,不能保证所有劳动者劳有所得;它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打非扫黄,却不能扫除黑社会;它能够制订法规和投入资金,却不能遏制环境污染和破坏。政府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似乎更多表现在“救火队”功能上,在防止“失火”方面则越来越捉襟见肘。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政府很可能丧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控制,一旦出现更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例如经济或政治危机,它是否能有效化解也就越来越难以确定。
三、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上分析表明,这些变化使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前的中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却算不上是一个“正常的”或“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因为那时的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拥有社会主义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道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拒绝作为国际分工低端链条的一环而未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其他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取得的经济社会进步。同时,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在国际上具有与人均收入水平不相称的世界影响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GDP增长较快以外,中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体制和社会表现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几乎达到有它们之所有、无它们之所无的程度。中国宪法的序言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宪法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宪法第六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其他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拥有这样的宪法。然而,现实往往比宣言更有说服力。中国的改革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于这个“特色”到底是什么,三十年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国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中国今天的现实。从一个“正常”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现象不但很容易理解,而且几乎都能轻易找到答案:用计划经济或历史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准衡量,改革后出现的大量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甚至匪夷所思,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这些现象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却不但完全正常,而且必然如此。因此,继续用传统社会主义的有色眼镜观察当今中国现实,难免陷入认识误区。
认清这一点,还有助于认识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回归“正常”,意味着丧失了原有的基本制度特色,走上了常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对中国而言是福是祸?中国能够沿着这条常规道路“和平崛起”,或者说,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已经变成一个“正常”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最适当的参照当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1949年之前的历史经验。如此看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景并不乐观。
当年,中国革命不但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实现国家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富国强民。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就不能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后尘、因循守旧,而必须打破常规,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9]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以利润为中心,全国一盘棋,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好工业化基础,这正是为中国超常规发展所开辟的蹊径。中国在短短20多年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证明当时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基本上行之有效。在计划经济后期,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时间被定在20世纪末。事实上,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提出,凭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应该而且有可能用五六十年超过美国。[50]现在看来,这个目标似乎过于野心勃勃,但当年并没有遇到多少质疑,而且,根据建国后经济超常规飞速发展的经验,这个目标似乎并非高不可攀。当然,方法必须是打破常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51]
可惜的是,历史在四个现代化蓄势待发的当口出现了转折,“本世纪(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止步于宏伟蓝图,人们也永远失去了验证该目标按照预定发展战略能否得以实现的机会。
改革后中国重建市场经济,再次拜西方为师,学习和因循市场经济规则,放弃了另辟新路的努力,进入了“常规”发展轨道。历史经验和大量研究表明,尽管或许存在所谓“后发优势”,但资本主义发展至今,能够按照常规路线发挥这种优势、进而赶超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发国家始终凤毛麟角。相反,绝大多数国家几百年来始终无法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一些一度高速增长的“明星国家”也难以摆脱“繁荣-膨胀-泡沫破裂-衰退”的怪圈,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始终面临“后发劣势”或“发展陷阱”。参照这些历史经验,人们有理由设问,回归到这条“正常”道路的中国具备怎样的特殊条件,能够避免重蹈这种始终不发达的“正常”轨迹,从中脱颖而出?
事实上,中国正在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短期挑战。在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已然问题成堆。在经济领域,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和关键企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逐步“殖民化”,人力资源优先服务于外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存在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现实危险。在世界经济史上,依靠外资实现现代化的例子绝无仅有,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所谓新兴工业国。在中国,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经济模式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了革命,那么,重新回到这种模式的结果很可能同样难以避免类似的困境。在社会领域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加速的两极分化、加剧的劳资冲突,以及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却越来越陷入苦无良策的境地。一些所谓关注“民生”的措施尽管能够缓和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矛盾的根源,正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局面一样。另外,市场化改革导致社会分裂,理想信念破灭,道德价值沦丧,不再能够同心同德,形不成统一意志,大大降低了整个国家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因此,即使中国的经济仍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正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更为严重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由增长转为衰退只是时间问题。作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已经没有任何特殊武器能够有效应对经济减速或衰退带来的后果,例如危机时期通常出现的银行挤兑、物价飞涨、股市崩盘、失业剧增等,而连年积累的各种矛盾例如官员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很可能集中爆发,甚至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这些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最幸运的政府也只不过能够把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持在低烈度水平上,避免全国规模的爆发,其他国家则不得不忍受长期社会混乱、内战甚至分裂。沿这条常规道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不会比这些国家更幸运,只要看看1949年之前的历史就很清楚。未来中国如果发生类似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其后果只会更严重,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身受其害的人口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迅速实现现代化,尽快成为发达国家,就是保持社会稳定、不出现全面倒退可能也相当不易。
居安而思危,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我们应该对改革认真总结和反思。本文认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对改革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应该以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对未来改革走向的判断也应该以此为依据。
注释
[1]相关争论,参见路爱国:《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一些评价和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8-117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3]在这里,发展中国家主要指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有时被叫做“世界南方”。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的生活水平较低或非常低下,工业基础不发达或非常薄弱,人类社会发展指标通常远远落在后面。
[4]引自卢周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人民网,2007年05月2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5792601.html。
[5]黄孟复、胡德平主编:《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刘日新:《2004年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剩下15.3%了》,2007年1月18日,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985。
[7]新华网北京2008年2月28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2/28/content_7689532.htm。
[8] 有关民主排名,见存文: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06”, in World in 2007; freedom house;以及VP 文。
[9]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洞见的新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打压和试图和平演变的目标,准确地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因素”。所谓共产党因素,就是试图在全人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它把跨国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人类实现大同作为自己的目标。见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平演变的目标是‘共产党因素’” 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2395199&bid=2。
[10]中国社科院发布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
[1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12]沙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13]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年),2005年中国与这些国家一道被划入低中等收入国家一类。
[14]参见路爱国:《增长与发展辨析》,载李向阳主编:《世界经济前沿问题》(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83-607页。
[15] Chang, Ha-Joon,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6]参见:江小涓:《理解开放与增长》,《比较》,第26辑,2006年,第1-24页。
[17]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及中文版前言,“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18] 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 January 2006,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Chinaexports.pdf
[19]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已与美国持平,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了美国。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从1978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
[20]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45-60页。
[21]联合早报网,2007/8/8。
[22]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3]《中国新社会阶层具八大特征聚集大部分高收入者》,http://www.sina.com.cn,2007年06月11日03:37,人民网-人民日报。
[24]美国《富布斯》杂志2007年3月8日发布,上榜者分属于55个国家/地区,其中美国人最多,高达415人,其次为德国55人,以盛产暴富寡头著称的改制后的俄罗斯位列第三,印度以36人上榜名列第四位,第五位和以后依次为英国29人,土耳其25人,日本24人,加拿大23,香港21,台湾8人。
[25]《据统计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http://www.sina.com.cn,2007年12月31日01:41,《新京报》。
[26]求是《小康》杂志社主编,全面小康蓝皮书《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7]参见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例如在委内瑞拉,无产阶级的数量相对有限,约占人口的10-15%;农民和农业工人约占经济活动人口的10%;人数上最多的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几乎占了人口的50-60%。见[比]波尔•德•博斯:《委内瑞拉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性步骤(上)》,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第9-16页。
[28]参见张勤德、陈寒鸣编著:《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香港: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
[29]《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5-1,国家统计局。
[30]参见《三峡都市报》,记者吴雅娇,2007/3/25。
[31]见全国妇联2008年2月28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802/t20080228_504717806.html。
[32] World Bank 1980:110-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33] UNDP, 1994:105 and 10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34] 见Dreze, Jean and Amartya Sen, 1989,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Press; Sen, 1995: 15, “Mortality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Failure”,Innocenti Lectures, Florence, Italy: UNICEF;相关讨论,见Lu Aiguo, 1996, “WelfareChanges i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Research for Action 26, UNU/WIDER,Helsinki.
[35] World Data Base.其他来源的数据显示类似的变动趋势,例如:05 Little Data Bookfor the 1990s, pp.8-22, and 64,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36] 05 Little Data Book, The World Bank, pp.8-22 and 64.
[37]见巴德年委员在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九位两院院士发言,2007年3月11日新华网。
[38]《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2005/html/0105.htm
[39]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4月2日报道。
[40]中国政府官员认为,经费不足是扫除文盲的主要障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扫盲教育处主任高学贵指出,中国的文盲已经出现地域性特征,他还说,目前中国的扫盲经费只有8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个文盲只能分配到7分钱,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见《侨报》,2007年04月03日。
[41]余天心、王石生:《中国政府行政成本有多高》,《改革内参》,2005年第12期。
[42]《瞭望》,2007年03月31日。
[43]孙立平:“基层政治是如何溃败的”,200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网,转自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07/21876.html。
[44]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国发[1994]30号)。国务院制定和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布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7年时间里,基本解决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
[45]洪大用,引自《城市贫民阶层是一个信号》,2007年1月9日,南风窗。
[46]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3月至5月对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组报告显示,有2700万孩子未完成义务教育。《中国农村‘普九’欠债500亿》,2007年06月29日,新浪网;及同日新华网。
[47]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讲话。
[48]周弘、张浚、张敏:《外援在中国的特征、作用和意义》,《世界经济调研》第24期,2007年7月2日。
[49]毛主席写在周总理三届人大报告里的一段话。
[50]毛主席在1956年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
No related po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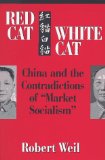
An excellent paper! But I don’t agree with some of the author’s arguments on China’s achievement on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before 1978. Since the average death age and infants’ death rate were extremely low in China because of wars before 1949, it was not very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se two rates. Even without the 1978 reform, the increasing speed would slow down. This fact has little to do with particular policy but a natural process alo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